爱游戏电竞中心 News 分类>>
爱游戏电竞下岗、离婚、抑郁后52岁阿姨骑自行车环游世界
当我们想象一个五十岁女性的生活样貌,场景或许是这样的:帮忙料理家庭、照顾孙辈,忙碌到晚上得了闲,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。
但在李冬菊这里,妻子、母亲、祖母,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,她最愿意谈论的,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,是个骑行者。
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。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,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,后来丈夫外遇,被迫离婚,患上抑郁症。在经历这一切后,52岁那年,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:骑车,上路。
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,经济上依赖丈夫,生活上依赖儿子,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,更别提出国了。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。此后的八年间,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,她骑过三个大洲,十五个国家,爱游戏电竞数以百计座城市,拍下了十七万张照片。
李冬菊否认自己是一个“出逃”的女性。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,而是为了求生,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,重新活过。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,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:年过半百,独自一人爱游戏电竞,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。这一刻,爱游戏电竞她就要上路去。
李冬菊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。最开始,她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“骑行”这项运动,毕竟,她已经不再年轻了。
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,飞驰而过的骑行队,她还是艳羡不已。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,“就只是觉得好帅、好神气”。
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,是买了个骑行头盔—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,自己在家戴着过过瘾。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,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?
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,给她买了辆车。吉安特折叠山地车,一千一百元,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。那是2014年,李冬菊52岁,她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,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。
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。她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,从西边骑到东边,想借此结识些骑友,希望能带带她。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她攀谈起来,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。机会来了,李冬菊找到队长,却被严厉地回绝,“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?”
她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。自己没有经验,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,年纪还大,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她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,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,装备不行。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四五千元,李冬菊一千多的车“骑长途根本不行”。
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。她不再在线下寻找,转向了互联网,“因为你心里喜欢这,你又不敢说,说了还老被拒绝。”她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QQ群,不多时,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。
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,李冬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汇合,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。在此之前,她连郑州都没离开过。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一千多元办好四国签证,毫无准备,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。
虽然稀里糊涂地,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。只是没想到,她又在半路被抛下了。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,各自有不同的标准,加上她年纪大,骑得慢,分歧一天比一天多。同行了一个星期后,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,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她说,“你滚吧”。
滚去哪呢?握在手里是部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,连网都上不了。情急之下,李冬菊拿着五万越南盾,向旅店老板连比带画,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。网友赶来把她安顿好,几天后联系人将她送回了国内。
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。四国里只到了越南,景点也没去几个,从出发到灰溜溜地离开,不过十天。但李冬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,“像毒品一样,尝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”。
于是她又出发了。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,她换上智能手机,学习怎么移动上网;把自己钉在电脑前,一天十几个小时地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,笔记写了几本子。找不到靠谱的队友,就独自出行,也不再好高骛远,从国内的城市开始。
儿子怕她孤单,送给她一只小狗,棕色的卷毛泰迪,儿媳妇起名叫犀利。她把犀利抱进车筐里,一人一车一狗,先是去了三亚,后又从西藏骑去青海,一路骑到新疆。2015年一整年,李冬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二十多座城市,到了2016年,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,她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呆了一个月,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。
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。2019年上半年,李冬菊花两个多月游览了欧洲六国,年中回到家,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。直到年底新冠疫情爆发,这才宣告结束。
骑行的过程,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。她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,机械性地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,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。欧洲的住宿费高昂,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,她便自己搭帐篷过夜,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,她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。
危险也总在发生。她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,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舍,心里觉得不对劲,给大使馆打了电话,才知道这是黑店,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。
离险境更近的一次,是在澳洲的某晚,她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,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——那是她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。通常情况下,她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,但就那一晚,兴许是太累了,她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,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。迷迷糊糊中她被灯光和人声唤醒,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,李冬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,也觉得后怕,还好是睡在了隐蔽的小树林里。
说起这些故事,她语速飞快,话又多又密,一股脑儿地倾泻出来,仿佛在心里排演了几百遍。李冬菊珍视它们,那几乎是她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。
而李冬菊人生的前一半,和大多数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女性没什么两样。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,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,被分配去农场,因为身体不好,在炊事班干了四年。从农场回到城市后,赶上工厂招工,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。
她爱钻研,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,她每天都提早一个多小时上班,仔仔细细地挑拣开;手也快,厂里其他人三四个人才能打一台车,而她自己就能打一台,产量时常是别人的两倍。那时她评过厂里的模范标兵,工资每月能有一百多元,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二十多元。
后来儿子出生了,丈夫又开始频繁出差,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。纺织厂三班倒,工作强度高,为了照顾家庭,她换了份清闲的差事,调到汽车制造厂,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。
时间迈向新世纪,劳动制度改革,铁饭碗被打破了。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,李冬菊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。44岁那年,她正式从企业内退,失去了工作。
与此同时,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,升职为中层领导。在她下岗的第四年,丈夫外遇,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。直到出轨对象给李冬菊打来电话,她才知道这码事。
丈夫提出要离婚,房子归李冬菊,自己把钱带走。她气急,说人都没了,要什么钱和房子,丈夫顺势问她,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。那会儿李冬菊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,“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,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”,于是说着“为什么不敢”就签下字,按照协议上写的,自己什么也不要。
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,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。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,李冬菊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,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:人长得帅,体贴又细心,“像白马王子一样”。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,她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,他保管物资,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,常常去他那儿领面,他低头时,眼睫毛又长又卷。
离婚后的三四年,李冬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,觉得天都塌了。在她原有的观念里,嫁鸡随鸡嫁狗随狗,就算两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,那也是可以解决的,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?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,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?她很难描述那种感受,觉得愤怒,又觉得伤心和茫然。
那段时间,她每天只能睡着两三个小时,吃安眠药也没用,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;白天见着个人,话说不过两句,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,“像祥林嫂一样”,时间一长,身边人都躲着她。儿子见她“眼睛都直了”,把她带去医院精神科,确诊了抑郁症。
医生给她开了一大包药,靠着这些药,李冬菊起码能吃能睡了,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。她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,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,只是一停下来,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,折磨得她坐立难安。
药的副作用大,对心脏不好,吃了一段时间,李冬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,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,把牙都磕松了。经过这回,她擅自停了药。没停几天,眼又直了,儿子赶紧送她回去复诊,医生说她的情况很严重,得终身服药。
但最后她还是把药给停了,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。开始骑行后,她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,直到16年出国,她连药也忘记带,却没再发作过,李冬菊想,是“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她”。
从下乡到下岗,再到离婚,李冬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,被推着往前走,从没有自主选择这回事。那些年发生了什么,很多她已经想不起来,也不愿细想。
从她52岁第一次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,她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:她要出发。
在李冬菊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,又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。后来我们都知道了,那是网名叫“50岁阿姨自驾游”的苏敏。李冬菊不想与之相提并论,她不痛恨家庭生活,没那么坚决,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。她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。
李冬菊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。丈夫是中层领导,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,也从没操心过钱。儿子懂事,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,她都能听儿子的安排。依赖着丈夫和儿子,她形容过去的自己“无忧无虑”。
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,她只需要按时上班,稍微打扫一下,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。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,几乎不和人打交道。下班后的生活,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。
就连骑行,最初她也有恐惧。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她第一次骑车,早在儿子上小学时,他们一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,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,七十里地,骑了一天。那次体验并不美好,丈夫儿子体力比她好上太多,她刚追上,他们就又出发了。她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,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。等回到家,连着好几天腰、腿、手腕,哪哪都疼。
她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,又累又苦,连照片也没拍一张。直到2015年她骑行青海湖,在她“哐哐”赶路赶得几近崩溃的时候,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,心里一动,干脆也去躺下休息。一聊天才知道,他们都是来徒步的。李冬菊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,纯靠走吗?那得多慢呀。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,“如果纯粹为了赶路,为什么不坐车呢?”
李冬菊被问倒了。她恍然反应过来,自己是独行的人,快或者慢、什么时候停下拍照,可以全凭心意,她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。从这天开始,她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,“风景在路上”。
上路就得花钱。过去她对钱没概念,从没有攒钱的意识。从东南亚回国后,她本想立刻骑往西藏,去银行取钱,一看存折,才170元。她不愿再花儿子的钱,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,她干脆去了丽江,开始打工生活。
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,同组的年轻人把活都推给她干,她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,心想自己这把年纪,为什么不在家享福享乐,要在这自找苦吃。可哭完她又转念想,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,是为了攒钱旅行。“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”,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。
在那儿做了三个多月清洁工作,每月工资一千八,都被她攒了下来。不仅实现了“经济独立”爱游戏电竞,临近过年,她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,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,“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”。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,见面就喊“奶奶,灰机”,李冬菊笑得合不拢嘴。
退休金每月三千多,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,靠着这些积攒,她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。至于穷游的办法,多琢磨总是有的。在欧洲的时候,她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,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,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,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,她能吃两顿。
她也感受到,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。骑行澳洲时她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,修车修的她满身油污。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,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她手中夹起。她也觉得自己邋遢,难堪得不行。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,同她打招呼,主动下车拥抱她,“你觉得自己脏,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。”
她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。骑过布里斯班时,她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,下车往前走了一百米,看见有黑烟升起。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,她担心是火灾,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。路上遇到本地人,李冬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,把他们带去一看,确实是着火,打电话叫来了警察。
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冬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,全城的人都认识她了。骑到哪儿,都有人冲她喊“hello!”给她加油。中途她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,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她骑行必经的路口,等了半天就为了给她一根充电线。她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,只是觉得“好开心,好自豪啊。”
回想上路的动机,其实非常简单,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。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,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她的臂膀,拓展她的野心。如今她已经64岁了。年龄、金钱,依旧没法阻拦她。等疫情逐渐稳定,她计划开启自己的环华骑行之旅,为了再一次看到更蓝的海水、更绿的草原,和更广阔的世界。
今年,她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。她在中原地区长大、生活,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,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她眼前时,她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:“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,那墨水般的海面,不夸张地讲,就像丝绸一样柔和,微荡着涟漪。一望无际的大海,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,除此以外一片静谧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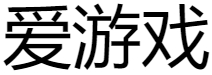 爱游戏电竞
爱游戏电竞 2023-03-04 06:08:44
2023-03-04 06:08:44 浏览次数: 次
浏览次数: 次 返回列表
返回列表 友情链接:
友情链接:





